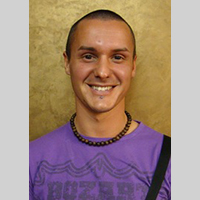手术日期:2009年5月。
![]() 意大利人
意大利人
我的名字是迪亚各,我是小脑扁桃体下疝的患者,我是在2003年一次呼吸停止发现我的疾病的。我被送到Piove Di Sacco医院的急诊,在一阵心肺复苏术后,我住院做了详细的检查,最后被诊断出这个我不认识又很奇怪的疾病,我当时很对于医生们用”奇怪”来形容这个疾病感到相当的害怕。
我出院后,我带了我所有的检查结果到神经外科,希望医生们能够解决或治愈我的病,因为虽然是个奇怪的疾病但也不是个完全性不被认知的病。
在我的家庭医生推荐下,我预约了神经外科主任S医生的门诊,到了门诊当天,我把我所有的病例资料都拿给S医生,我当时和我的母亲一起去的门诊,她陪我走过了我漫长的求医路程(尽管很担心但她也很坚强);那时医生开始平静的看我的核磁共振片和Piove Di Sacco医院的报告,我原本极度害怕的心情也平静了一些,医生告诉我这不是什么太严重的问题,这个病就像是阑尾炎一样,只需要在后颈开一个小小的口,是一个简单的手术,住院一晚之后就可以出院回家了(我发誓这些话是医生亲口所说,我都深深的记在我心里);此外,医生还拿了一张纸画了一个小图画来跟我解释这个疾病和手术,医生跟我说:”您想想,我们甚至都不用剃掉你的头发。”(但当然的,头发并不是我所担心的事),不管如何,那时医生的态度给了我勇气,医生跟我说等他们一有手术空缺就会马上通知我,最后我付了190欧元的门诊费,因为是私立的门诊,且S医生也是当地最好的神经外科医生,公立的社会医疗不涵盖私立的门诊。
之后的一个半月我又回到了以前的生活,但不久我母亲就给我打了电话,我母亲要我赶快从公司回家,因为医院有手术空缺了。我回到家,打包了简单的行李就马上到医院的神经外科报到。
我是在2003年7月16日去的医院,医院帮我预订了手术当天的病床,隔天我做了所有术前需要的检查也签了手术同意书;在这之后8天,在2003年7月24日我进行了枕骨减压并颈1椎板切除术,手术名称很容易写下来或说出来,但我和您们保证要面对和承受这个手术不是那么的容易。
术后,我在加护病房醒过来,全身插满了管,无法动弹,当时我能动的只有我的眼睛(我心想:不是说只是个简单的手术吗?)我不知道医生们到底确切为我做了什么,也不知道手术进行了多长时间,刚醒过来时,我甚至都还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究竟在加护病房待了多少天,但这一切都让我不再相信S医生和我说的一切。
整天待在病房害怕的看着天花板的心情是非常糟的,我甚至都不知道日子过到哪一天了,也不知道我在病房多长时间了,更不知道我到底怎么了,也不知道手术是不是成功…这些问题就一直重复不断的环绕在我脑海里。不过在出了加护病房后,我开始慢慢理解真相;我向您们发誓住院的那段时间是非常痛苦的。
换到普通病房后,我一直高烧不断且有剧烈疼痛,手术的伤口不如我想像的小(直到现在我的后脑还是清晰可见那道伤口),我的身上插满了针,还连接了一个侦测生命迹象的机器,另外还有奇怪的机器一闪一闪的在控制我的身体状况;我不知道也永远不可能知道医生们在那次手术到底对我做了什么,我只知道我的大脑有一个塑料硬膜,其他的我都不知道了;我只记得术后带来的痛苦和后悔,术前门诊医生所说的都是骗人的;我和您们发誓,我当时还很勇敢是因为我看到在我周遭的都是比我更严重的重症患者:如肿瘤患者、血管瘤患者等。
但我错了,因为我当时还不知道我的情况或我的疾病有多糟;我在医院一共待了13天,我是在2003年7月29日出院的,回到家后,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我的情况非常糟。
在家休养的时间非常长,我不知道确切在家待了多长时间,但我可以确切的知道我的痛苦有多多。但我自己鼓励自己说,在经过那样重大的手术后,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我还是一样一直高烧不断;打一个喷嚏,我的脑就像要爆炸了,我真的快疯了,我一直祈祷我不要打喷嚏或呕吐,这是最糟的2个动作。
我没多久就赶快回医院检查进了急诊,医生们不懂为什么我会高烧不退,他们开始思考手术的风险和禁忌;医生们不知道是我对植入硬膜的材质过敏或有抗拒;但我很清楚的是医生们想再对我开一次脑的打算,希望能藉此找出问题。
但我已经精疲力尽了,不管是心理还是生理上,我拒绝任何更多的折磨或治疗,我真的不想再有更多的痛苦了。
后来医生决定尝试进行药物治疗,当医生在脖子为我注射药剂时,我可以感到疼痛的减轻,不过随着时间我也慢慢的感觉身体比较好一些了,感觉好想最糟的部分我已经撑过去了,我痛苦的回到了一个平常但身体有疼痛的人生。
之后几个月我从拍了核磁共振片等检查,检查结果看起来一切良好,重新回想再忘记发生的一切是很难的,但在手术后3年,我恢复了身体的力量和意志力。
但好景不长,突然有一天我的疾病问题又都再出现了,透过我的家庭医生我做了很多检查,但每个检查的结果他都说很正常,减压手术的成果很好,但事实是医生们让我做了一个又一个没有用的检查,最后医生们更告诉我,这是我有精神问题,他们如此坚决的态度让我也真的相信是我自己脑子有问题!
我疯了,但我其实不是真的疯了,而是医生们不认识我的疾病和它病症的恶化。 我后来只好接受一个朋友的建议到了一家治疗抑郁症的医院,因为那时的我非常忧郁,我甚至两次尝试自杀,我很迷惘也感觉自己很没用,觉得自己是家人的一个负担。到了抑郁症医院后,我遇到了M医生,我告诉了她我的情况,她最后决定让我住院,我已经不记得我入院的日期了,但我当时遵造着朋友的建议住院了。
对我来说,从住院的第一天开始,我就觉得我好像在监狱里,每天都要吃一堆对我没有任何用处的药,同时我的病也一直不断的恶化,但我也因此变的更坚强,在医院里我也认识了很多好朋友,他们需要的是有个人说话来忘记他们的痛苦;不过虽然有了这些好朋友,但我的病还是一直在恶化,我本来不抽烟的,但在这我也开始抽烟,每天3包烟;我就像在一个笼子里,被剥夺了自由;现在我还跟医院的几个人有联系,他们很感谢我当时陪在他们身旁。
后来医生给了我一些药物让我可以在家进行疗程,但需定期做精神控制的回诊;我虽然回了家,但我的生活非常痛苦,我的疼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不过尽管如此,我回到了工作岗位,我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我服用的药改变了我的个性,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我坚强、努力的继续我的生命。
我一直到2008年都还继续回诊和做检查,但这时我的疾病已经开始使我的身体退化,我以前体重85公斤,后来降到65公斤,我瘦了20公斤。我的人生非常的低潮,我远离一切和所有人,我的身体开始没有感觉,身体左侧也开始半瘫痪,对冷或热没有感觉,我在工作时受了伤却都没有感觉,都是看到了血才知道受伤了。
我开始很担心,也去看医生,但医生们都还是一直重复这是我精神问题。我真的没法再忍受下去了,我在不了解我的疾病也不是医生的情况下,自己开始在网络上搜寻资料和信息。
透过网络,答案终于出来了,我患的是一个相当奇怪的病,所以大部分的医生都不知道该怎么治疗它,但我找到了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一家研究所,感觉他们很了解这个疾病并能治疗它,于是我决定透过电子邮件联系巴塞罗那Chiari研究所。
一开始Chiari研究所答复了我的邮件,他们让我把我所有的检查报告片子都发给他们,诊断我的病例是否是罗佑医生治疗的对象,也评估我是否适合终丝切断手术;在此同时我又去了一次我们当地的神经外科医院,我告诉医生到西班牙治疗的可能性,但医生否定了这个可能性,他不了解我的疾病,而根据他说,没有任何意大利的医生会为我进行终丝手术治疗;我听了医生的话,但我唯一感兴趣的是为我的痛苦画上句号,我必须再试一次。
因此,我到了西班牙到了研究所,我认识了罗佑医生,医生帮我进行了门诊,我没有任何精神方面的疾病,而是我的疾病发展的很严重了,罗佑医生让我在希玛医院做了一些检查,结果发现我除了小脑扁桃体下疝外,还有脊髓空洞和脊髓牵扯现象(导致我的身体左半侧瘫痪),胸部脊柱侧弯和颈椎生理曲度变直。此外,罗佑医生告诉我,终丝牵扯脊髓的情况也对我造成了6个椎间盘突出,2个颈椎的,2个胸椎和2个腰椎的。罗佑医生告诉我手术并不能解决消除所有疾病已经造成的伤害,但手术对我能有好处,他建议我进行手术,但一切都必须先确定我在意大利手术时植入的硬膜没有问题才行;我的疾病已经发展的相当严重且对脊髓造成很多损伤了,但我求医生让我做手术,因为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最后我做了手术,手术约进行了30分钟,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心情很振奋的下了床,隔天医生帮我安排了回诊日期后我就出院回家了。虽然身体疼痛还在,但我感到生命更有力量,我遇见了坦白、诚实又亲切的医生;术后一个月我回到研究所复诊,虽然路途遥远些花费也多,但感谢罗佑医生,我再次对生命感到活力;到了西班牙复诊时,医生对我术后的恢复成果感到相当惊讶也很高兴。
复诊时,我跟医生说我的腿有行动问题,医生告诉我这是因为腰部椎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造成疼痛的问题,建议我日后可以再做检查以确认是否需要进行射频神经切断手术来消除我的疼痛问题。
我非常感谢罗佑医生和他的医疗团队,谢谢他们给了我希望和重新活下去的力量,谢谢你们大家!
迪亚各
我的信箱: [email protected]